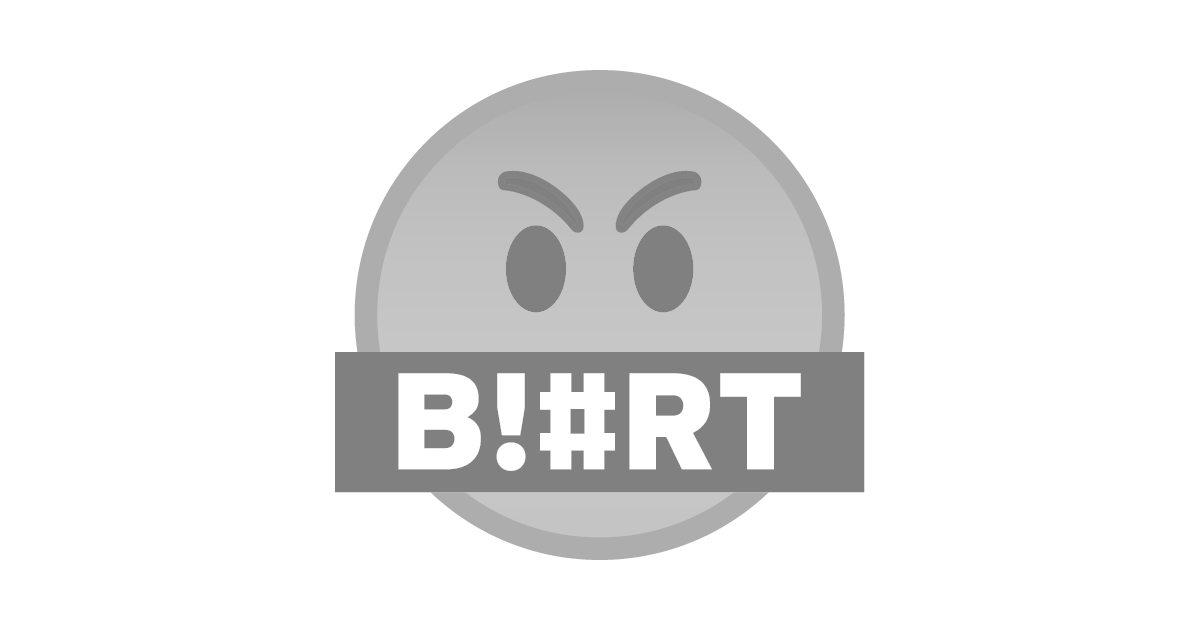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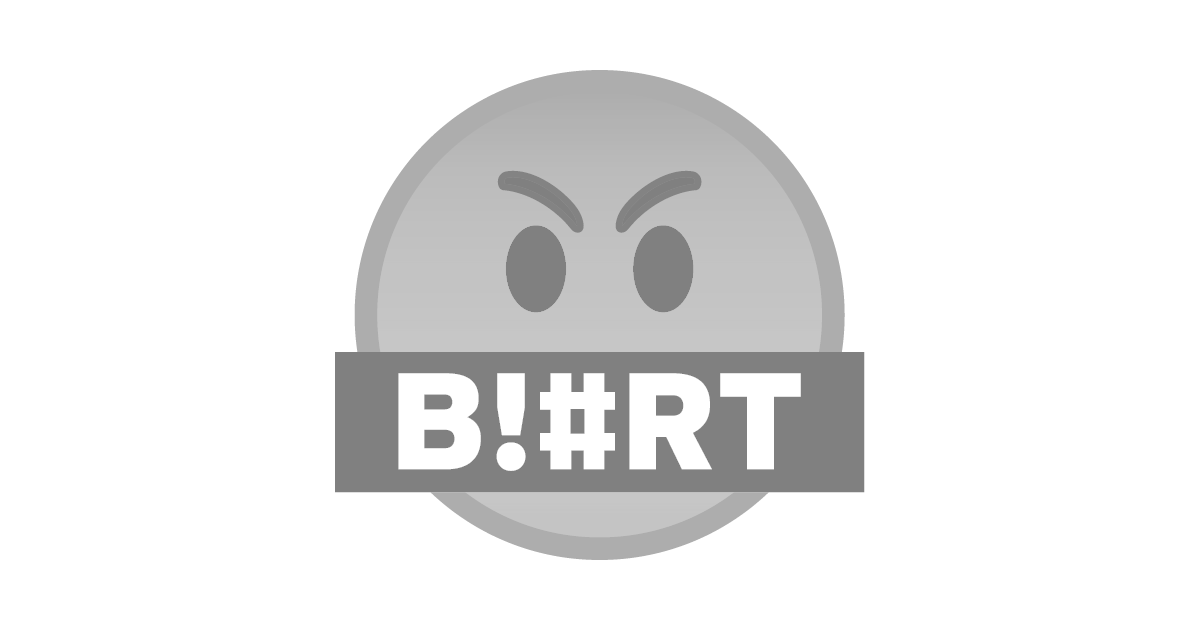
有多少人清早起床朝着目标出门,
和身边至亲道别说今晚想吃什么,
然后吩咐公司同事处理今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又有多少人有预感到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自己生活的家中道别?
两年前干姐姐去世那一年,
她孩子告诉我说当时干姐姐正在洗澡,
然后突然头晕的大喊自己丈夫说意识到自己中风了,
要家人赶紧送自己去医院救治,
那一刻干姐姐意识还是清醒的,
在进入昏迷无意识之前,
仍然以对自己仅有身体控制能力,
以口齿不清的语言能力交代孩子紧急的处理钱的问题,
你问我的话,
我至今还是有点生气的说当年为什么两天后才让我知道?
虽然我即便是知道了也做不了什么,
当我知道真相去到医院后发现,
干姐姐像是好好的一个人昏睡在病床上而已,
我走过去用糖尿病测试的针笔,
给干姐姐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刺针放两滴血出来,
再从耳珠放了两滴血,
我告诉干姐姐的孩子们别太担心,
我爸中风了三次也是这样挺过来的,
我当时还在干姐姐眉心部份画了个圈,
干姐姐当时还震动了一下。
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椅子上对干姐姐的丈夫说,
你要有心理准备的接受即便是将来干姐姐康复以后,
毕竟是脑受损,
像我爸一样,
再也回不到从前你们所认识的那个人的性格样子了,
我姐夫不以为然半信半疑的神情看着我,
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或者是他并不接受,
一个没有和中风病人相处多年的人,
我很难给对方说的清楚的,
毕竟针一直以来并没有扎到自己的肉,
自己一点都不疼的,
第二天才发现干姐姐情况事态严重,
并没有人告诉我,
因为当时乐观的我感染了他们?
还是他们并不忍心即刻告诉我和内子真实情况?
原来干姐姐右边脑神经出血,
再到左边脑神经出血,
加起来的量有一杯左右,
我当时听了后身体凉了一节,
我爸虽然三次中风却只是出血一个铜板的大小而已,
干姐姐的情况让我知道我内心要有心理准备了,
不妙啊!
医生本来说要等干姐姐三天进去深层昏迷醒过来之后立马给她做开脑手术,
干姐姐醒过来那天凌晨开始进入了剧烈的震动和呕吐,
阿根打电话给我说让我过去医院见他母亲最后一面,
我当下犹豫了,
既然是最后的时间,
不如留给他们家人相聚吧,
我选择了不去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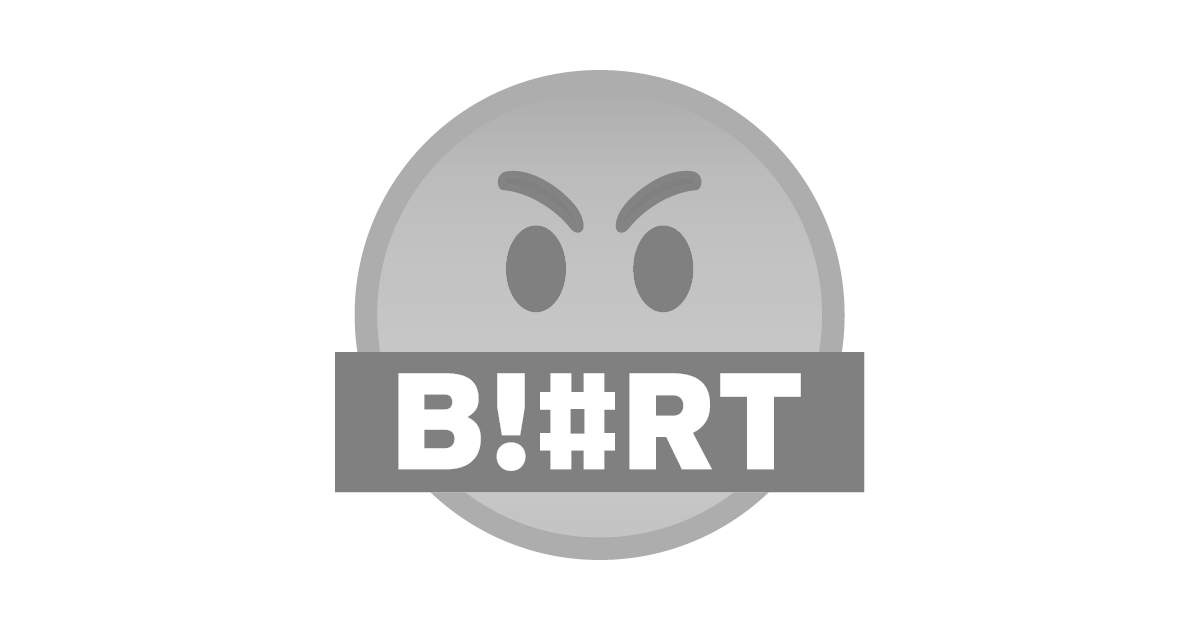
三十五年前,
开酱油厂的舅舅要送酱油去二三十公里的偏远郊区,
经过一段山路因为躲闪牛群而发生了车祸,
舅舅的车撞向山边被驾驶盘顶着身体大量流血,
意识清醒的舅舅让情伤的助手赶紧去打电话报警,
在那个荒郊野岭又没有手机的年代,
更别说荒郊野岭会有公共电话了,
因此舅舅因为失血过多而命殤于车里,
当年的棺材就像是林正英电影那样的棺材,
十二岁胆小的我不敢太靠近棺材看舅舅,
平常就无比威严的舅舅,
此刻更是不太敢多看,
虽然最终我还是看了几眼
就像是林正英电影里面的僵尸一样的样子,
那个年代可能没有做下颚处理,
又或者是舅舅因为断气太久而导致下颚没有合起来,
你能想象到吗?
似乎每个大家族都有个复杂的家庭关系,
在那个三妻四妾的年代里,
我是二房的子孙,
复杂关系,恩怨情仇,
并不因为大家族有钱没钱的,
外公依现在的标准看来算是中等家庭阶级吧?
开酱油厂的,没钱你信吗?
当年二战前有一两房妻子似乎是很普遍的事,
小舅舅就是大房的儿子,
童年时的小舅舅在香港居住过好几年,
我至今记得当年小舅舅说,
当年外公带着他在香港海边吃点心,
吃完后就顺便把碟子丢进海里🤭
这样就少算很多吧?
似乎鹤山人讲话都像是骂架一样的吧?
我没见过外公,
大人告诉我外公在我两岁时就过世了,
我奶奶说是她带着两岁的我去送外公的殡,
似乎人走茶凉的让我意识到必须为已经离开人世的他们写下一点文字记录,
希望好事越来越多能让我少处理,
以至于能静下心来写出他们依旧留在我心里的点点滴滴。
好,就写到这里吧。
送你一首我唱的歌听听
歌名叫有故事的人